茫茫青藏线,巍巍国土人
7 月 1 日 ,凝聚着中华民族智慧与血汗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了。为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所的几代科学家在青藏高原上艰苦奋斗,监测地应力,考察断裂带,研究冰川,寻找水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地质成果,保证了这条天路的顺利贯通。在极度缺氧的世界屋脊,他们品味过饥饿、寒冷、病痛,对抗着洪水、风沙、野兽,体会了恐惧、孤独、无助。但这些都不能让他们停下前进的步伐。他们把青春与血汗留在了青藏高原上,把骄傲与自豪留给了国土资源人。当青藏铁路的第一班车在万众瞩目中拉响汽笛的时候,他们一边默默地为祖国祝福,一边仍在远离人们视线的地方无私奉献着。在此,我们特地选取了几位曾战斗在青藏铁路一线的老、中、青年地质学家,展现他们精彩的人生片断。尽管篇幅有限,不能描绘他们完整的地质人生,也不能呈现所有地质工作者的艰辛历程,但通过这一幅幅剪影,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几代人前赴后继的身影,在历史的画卷中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
茫茫青藏线,巍巍国土人
徐峙 李晓明
易明初:我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今年 70 岁的易明初,是唯一参加过青藏铁路沿线两次地质勘查的地质工作者。“我是这条铁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他自豪地说。
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所响应国家建设青藏铁路的号召,组队奔赴青藏高原进行地质工作, 39 岁的易明初作为项目的负责人之一,踏上了青藏高原,一干就是三年。
当时条件的艰苦可想而知。没有新鲜的粮食和蔬菜,吃得最多的是压缩饼干;没有 GPS ,全靠考罗盘和经验认路;没有通信工具,与外界经常失去联络;没有便捷的交通工具,卡车只能走大路,其他的路全靠步行。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和高原的缺氧、低温、狂风、暴雨斗争着,和野兽、山洪、泥石流斡旋着。
1975 年 6 月 22 日 ,易明初和项目总负责人、当时 54 岁的胡海涛院士(已故)从海拔 3800 米 的三岔河工作站出发,穿过野牛沟中冰冷刺骨的昆仑河急流,不知疲倦地向前观察着各式各样的构造形迹,不知不觉中已经是晚上 9 点,太阳落山了。当时离驻地已经很远,天黑之前肯定不能赶回去,但如果留在这里,就有被冻死和被野兽吞噬的危险。借着夜色中仅有的一点光,他们一边手持铁锤和木棍防身,一边高声唱着《地质队员之歌》壮胆,拖着沉重的双腿,凭着地质队员特有的方向感穿过急流险滩,踏着无路的山坡攀登。就在他们快要精疲力尽的时候,忽然看见几束手电筒的光在远处闪烁,“胡海涛”、“易明初”的喊声在夜空中飘荡——总算遇到出来寻找他们的同伴了。当他们回到驻地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三点了。“当时没有任何通讯工具,在野外一旦迷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易明初想起往事,心里依然感慨万千。
三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换来的是丰硕的成果。青藏铁路三年选线的科学勘察报告,获得了 1978 年的全国科技大会成果奖。三年的高原工作,也使得易明初引以为豪的强壮身体受到了高原反应的巨大伤害。在下高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经常因为头晕而撞在墙上、地上,弄得身上到处是伤。医生甚至给他的家人下了死亡通知单。
就在易明初他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化为建设青藏铁路的生产力时,青藏铁路的建设却因为历史原因搁浅了。这一等,就是二十多年,易明初等得好苦。
2001 年,国家重新把青藏铁路建设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所主动承揽了沿线的地质工作。作为老一辈的青藏铁路地质专家,易明初被选聘为专家组成员和技术顾问。 2002 年 6 月,易明初瞒着两个儿子,谎称出差,重新登上了让他魂牵梦绕的青藏高原。到达西大滩的第一天,同行的项目组成员都因为强烈的高原反应而在驻地休息, 66 岁的易明初一个人跑了出去。他在自己 30 年前工作过的地方流连忘返,在这里看看地层,在那里看看断裂,一待就是 4 个小时。夜幕降临时,他恋恋不舍地走出了山坳,发现同伴们都在发了疯似的找他。“易老师,您怎么一个人到那边去了,那里有狼的。”易明初这才感觉到了后怕。
2003 年,易明初还想再上青藏高原,儿子和老伴说什么也不答应了,大夫也对他的身体情况说了“不”字。“其实我的身体很好,一点问题也没有,他们太胆小了。”事过多年,易明初依然耿耿于怀。这位 70 岁的老人身上,看不到丝毫向岁月低头的迹象。“我最大的遗憾就是退休太早,很多热量发挥不出来。”说到这里,老伴笑着插话了:“还早啊,你还想干到什么时候?身体还要不要了?”易明初也笑着和老伴抬杠:“我的身体棒得很呢,再干几年没问题的。”
采访结束时,易明初突然问记者:“你喜欢听歌吗?”
记者被问得摸不着头脑。“喜欢啊,怎么了?”
易明初说:“给你听首歌,《天路》,韩红唱的。我很喜欢,这些天每天都听。青藏铁路的通车,圆了我几十年的梦啊。”
说着他进屋打开了录音机。动人的旋律响了起来,他与老伴一人拿着一纸歌词,认真地听着,随着音乐打着节拍。当音乐结束时,他说:“我再给你清唱一遍吧。”说着,和老伴一起唱了起来:“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 / 看到神鹰披着那霞光 / 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 / 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 ”
他们的歌声不算十分动听,但歌声背后那炽热而纯朴的灵魂令人肃然起敬。
吴珍汉:临危受命的铁汉
关于吴珍汉的故事,很多都是从别人嘴里讲出来的。面对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说:“我没什么好讲的,你多写写他们,他们的故事多。”
2001 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所主动请缨,为青藏铁路进行应力测量、活动断裂分析、隧道稳定性分析等地质工作。 2001 年 12 月底,铁路建设部门紧急提出要求,在 2002 年 3 月 1 日 提交唐古拉以北至昆仑山一带近四百公里的 1 : 2000 活动断裂分布图,否则项目将转交其他单位。
1 : 2000 ,意味着铁路沿线任何一个 两米 左右的地质体都要清清楚楚地标在地质图上。而一二月份是青藏高原最冷的季节,在零下三十多度的极低温度和动辄七八级的大风下,生存都是问题。在这个时候进行大规模的地质工作,是史无前例的,更不要说完成这样紧迫的任务了。然而,为了青藏铁路,也为了地质力学所,他们别无选择。 2002 年 1 月,身为地质力学所副所长的吴珍汉研究员临危受命,亲自带着一帮“拼命三郎”上了高原。
项目组在数百公里的青藏铁路沿线分段驻扎,分头开工。作为项目负责人,吴珍汉既要统筹整个项目组的科学活动,又要保障地质队员的人身安全;既要参加具体的科学考察,还要兼顾所里的很多具体事情。因此,在项目组中,他是最忙碌的一个。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自己安排在最艰苦、海拔最高的唐古拉段,找地质构造最复杂的地方,所有的鉴定都要自己动手,所有的数据都要亲自综合,所有的报告都要亲自审定。因此,在项目组,他也是最辛苦的一个。从格尔木的驻地到昆仑山口的考察点,每一处都有他的身影,每天他都要工作到深夜。在极端的艰苦条件和繁忙工作中,这条铁汉的身体也累垮了。
春节后的一天,他赶回北京处理所里的事情,之后马上飞抵格尔木。一般人上高原,都要在海拔 2800 米 的格尔木适应两三天,但吴珍汉只在那里待了一宿,第二天就直接奔赴海拔最高的唐古拉,他放不下那里的工作。当天夜里 11 点多,在海拔 5060 米 的唐古拉兵站,与吴珍汉同住一屋的地质力学所研究员叶培盛突然听出他的肺音有点不对劲。在高海拔地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吴珍汉自恃在青藏高原多年,没当回事,但叶培盛不敢掉以轻心,硬逼着他下撤到海拔 4800 米 的雁石坪。没想到过了没多久,吴珍汉又回来了。任务太紧张,他不想当逃兵。到了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吴珍汉在床上翻来覆去,肺里呼哧呼哧作响。叶培盛明白,这是肺水肿的症状,再不治疗是会送命的。吴珍汉还想坚持,叶培盛坚决不答应:“你还要不要命了!”他马上联系好司机,带上氧气瓶,连夜把吴珍汉送回格尔木,这才保住了一条命。
这样生死攸关的事情,吴珍汉自己从来不提。在回忆起那一段艰苦卓绝的经历时,他只是笑着说:“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当时可真是玩命了,要不然可真完不成任务。幸亏有这样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队伍。”
由于这次工作提交的报告质量很高,铁道部非常满意,把接下来的地质工作都交给了地质力学所。因此,在此后的五六年间,吴珍汉每年都要上几次青藏高原,每次多则几个月,少则几十天,最多的一年竟然上去了五次。这样频繁地上下高原,会使心脏反复经受扩充与缩小的折磨,对人体危害极大。所里的不少专家就因此患了心脏病,有几位甚至在 60 多岁就英年早逝。吴珍汉虽然目前没查出什么大问题,但他自己很清楚,身体迟早是要还债的。他唯一的希望是,项目组的人将来别得心脏病。
“你不担心自己吗?”记者问。
“自己也担心,但是没办法,活得干下去。这是个要命的活,但不会马上要命。将来医疗费都要自己承担了,如果以后有人因为这个得了心脏病,还希望所里关照关照。”
这句话,让记者热泪盈眶。
叶培盛:感受生死时速
有八年小提琴演奏史的叶培盛,曾经的梦想是做个音乐家,但中考时却因为手太小而与音乐学院失之交臂。没想到,这双不大的手,在今后却将地质锤抓得如此之紧。
2001 年,叶培盛与几名队员一起在青藏铁路经过的当雄一带进行地质填图。他们从羊八井出发,穿过一条河去拉剖面。下午六点多,当他们返回的时候,冰川融水使得河水大涨。老式的吉普车在齐胸的河水中行驶,到河中间的时候走不动了。大家正要下水推车,年轻的冯向阳博士在这个时候突然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呈现出严重的高山反应症状。大伙赶快把冯向阳身体拉直,抬过头顶运到了岸边。紧急中请来青藏公路施工队的医生,医生一看说赶紧往拉萨送吧,不然没命了。可是车陷在水里,队员们连一部可以求助的手机都没有。危急时刻,从云南楚雄来的纸业老板贾树勋正好经过这里,他雇的两辆车中的一辆陷在水里,一辆正在岸边。见此情景,他赶快用自己雇的车拉上队员们往拉萨赶,并用自己的手机给拉萨 120 打电话求助。
走了几十公里的时候,由于车速太快,车底的钢板断了,抛锚在路上。附近正在修路,一天下来都看不见一辆车经过。大家刚下了车,就看见前方来了一辆车,一招手就停了,是国家林业局的。一看这种情况,他们二话不说,拉起大伙就往拉萨赶。车上正好有两罐氧气,抓紧为病人输上。走了不远,一个大土堆挡住了去路,怎么也过不去。路边正好有一帮修路工人,二三十个工人硬生生地把车抬了过去,使得路上一分钟都没耽误。又走了十几公里,两罐氧气输光了,这时拉萨 120 的急救车正好赶来。冯向阳得救了。
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叶培盛依然很激动。“冯向阳真是捡了一条命回来。那天真是太巧了,在路上一分钟都没耽误,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他可就真完了。”
冯向阳获救的意义不仅在于一条人命。贾树勋在回到云南后,专门给朱镕基总理谢了一封信,讲述了地质队员们生活、工作状况的艰苦,朱镕基总理做出了重要批示,使得地质工作者的装备得到了改善。叶培盛拿出自己腰间的摩托罗拉 v998 手机给记者看,“这就是那件事情之后给配的,当时还真不便宜呢。”这款曾经的经典手机,如今发短信如果超过 50 个字就会死机。
这样的“生死时速”叶培盛经历过不少。有时候,这位豪爽乐观的湖北汉子也会伤心、悲哀甚至绝望。有一次,叶培盛从当雄出发道无人区进行地质考察,和同伴约好了七天后的晚上八点在林州见。在山上考察的时候,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叶培盛把手表、罗盘等带金属的东西全部丢掉,趴在一个小凹沟里,看着一道道闪电一头顶劈过,听着一个个焦雷在身边炸响,心中一阵阵悲凉。“当时心里就想,要是在这荒山野岭被雷劈了,让人以为前世作了孽呢。”叶培盛笑着说。
七天后,天空中依然下着大雨。叶培盛从山上一路狂奔,到了约定的地点,正好晚上八点,可连接他的人的影子都没见到。原来同事见雨下得太大,以为叶培盛不会下来,便在几分钟前离开了。叶培盛看着空荡荡的高原,干粮已经吃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想放声大哭。没办法,只有扎起帐篷就地宿营,在饥饿和焦虑中等待第二天的到来。
“当时学地质的时候,真没想到有这么苦,不过也没后悔过。因为干这一行累起来真是累,但是可以到处跑,比别人看的风景多。那雪山,那冰川,那草地,太过瘾,太舒服了。”叶培盛乐呵呵地说。
他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想等孩子明年考完高中以后,带爱人和孩子一起去趟青藏高原。他要把铁路沿线的景物一一指给他们看,他闭上眼睛都知道它们是什么样子。
彭华:冰窟中捡了条命
今年 40 岁的彭华研究员,对佛法也颇有感悟,曾经专程到佛教禅宗的祖庭曹溪南华寺里住了七天,每天和寺里的老和尚讨论佛理。
彭华有一个奇异处,就是记忆力超人。他不仅熟知高原地质地理情况,而且对一路风土人情了如指掌,简直就是一部高原的百科全书。青藏铁路沿线每到一处,他都能说出其准确高程,拿 GPS 对照,分毫不差。沿路的河流的名字就仿佛印在他的头脑里似的,随口就来。大家都管他叫高原活地图。
和项目组的大多数人一样,彭华不大愿意说自己的事,讲起研究所的科研课题来却总是津津有味。让彭华讲出自己的故事一度成为采访中最大的挑战,因为他总是淡淡地拒绝。其实,这个具有纯粹科学趣味的人,胸中藏着无数的故事。
有一年冬天,彭华在楚玛尔河铁路特大桥下做物探,冬天的河面上全都结上了厚厚的冰,前面的人拉着电缆过河,听得哗啦一声,回头一看,彭华不见了。原来河里有温泉的地方冰很薄,身材魁梧的彭华一脚下去,踩裂了冰面,整个人瞬间没入了刺骨的冰水中。那时的气温有零下二三十度,被救出冰面没两三分钟,5到7级的大风吹得彭华全身立刻结冰,抖一抖,头发衣服上一起哗哗作响。
故事讲到这儿,听故事的人张口凝目,故事的主角彭华则像没事儿人似的插进来一句:你们猜猜看,我都在河里看到了什么?好多的鲹鲦儿,跟长江边儿上的一模一样。
这么危急的时刻,彭华居然有心比较河里的鲹鲦,而且说到自己就快变成冰雕大活人了,他自个儿先呵呵笑了起来,好像不是在说自己的遭遇。
后来故事讲完,我们才知道,要不是当时汽车就在附近,里面有暖风和一件军大衣救急,彭华难保没有生命之虞。即使当时的动作十分迅速,彭华还是患上了气管炎,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故事让人惊心动魄,唏嘘不已,但对彭华来说,这就是高原地质人的生活方式。项目组的 20 多位科研人员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高原冰山雪河之间的生死经历,只在谈笑之间作烟云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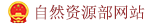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43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43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