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地质调查
我的地质调查生涯彻底结束了,止于2016年2月15日。我怀着沉痛又喜悦的心情来到办公室。沉痛的是我一个堂堂211大学地下水开发与可持续利用专业研究生的学术生涯就此结束,喜悦的是我终于有更多的业余时间来照顾我二个尚且年幼的儿子,作为一名母亲,我也希望把探索世界的梦想在他们身上延伸。
悲喜交加,难免生出许多感慨,勾起了我想要好汉重提当年勇的念头。
2006年我和我男朋友怀揣着为国家地下水开发与可持续利用建功立业的梦想来到了单位,但是由于我和他是学同一个专业,本着亲属不能在同一个部门的原则,他被分到水文地质调查室,我被分到了环境地质调查室,开始了我的环境地质调查职业生涯。搞过污染场地调查,干过地方病地质原因分析,为《水文地质手册》修编跑过腿,零零散散地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任务,也渐渐积累了些工作经验。2008年,我有机会作为工作内容独立开展工作,“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的时候到了。为了完成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我是一匹马”的誓言,作为项目组唯一的女同志远赴格尔木。
从海拔十几米米来到海拔近三千米的高原,再加上没有遮挡、刺眼的阳光,我有点头晕目眩。
项目工作紧张、有序。我们先是到地方部门收集资料,到当地相关部门开各种证明信,那时候当地政府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人少,经济落后地区的人要良善的多”的印象在我心里萌芽。
我们沿着青藏铁路沿线向两侧扩展25公里,对活动断裂、威胁铁路运行安全的隐患点、沿线油气管道泄漏点等进行了调查。调查的过程中虽然没有要渴死、饿死的经典悲壮镜头,但是变成非洲人,另加蚊子咬,嘴巴干到起皮和鼻子流血是家常便饭。
记得有一天,我们和格尔木水文站的同志集中取水样,我们的路线是从山前往绿洲带,这是我们的习惯,也就是距离驻地最远处开始我们的工作,逐渐向驻地靠近,这样的调查方式确保从早到晚越来越疲惫的我们距离住的地方越来越近,心理上会有些许安慰,也能确保我们更安全。到达绿洲带,已近黄昏。悠悠的白云遮挡了肆无忌惮的日光,绿洲带蜿蜒的小溪流熠熠发光,冒着泡的上升泉在深深的、浅浅的泉眼里更显神秘,尤其那口清澈的发蓝的泉,在周边绿草、野花的陪衬下更显静谧、悠远,深不可测。忽然松哥拍了我一下“嘿,又发呆呢”,这时我才回过神来,发现耳朵、手、脖子暴露在外面的部分都被蚊子盯上了。第一年出野外,实战经验还是略显不足,我们在当地地勘单位的帮助下,顺利完成了格尔木到南山口的实物工作量。
海拔继续上升,第二年我们只能驻扎在不冻泉了,我们租住的是文尕大哥和扎西大姐的简易房。高原反应和寒冷是此时野外工作的大敌。记得当时项目组为了避免大家产生高原反应,在格尔木逗留了大概一个星期才开始出发去不冻泉,当时我有些小感冒,也没有在意,就跟着大部队上去了,结果还是没能逃出稀薄空气的魔掌,感冒没好,反而加重了,头痛欲裂,水米不沾,但凡食物都没有了应有的魅力,那时候我都觉得恶心。当天下午,大家收队后,项目负责人决定把我送回格尔木治疗,在秀哥的陪同下,在格尔木输了3天液,又恢复了2天,我就活蹦乱跳地来到了不冻泉。“领导要来检查工作,我们给领导选一条冰川的路线吧,一是让领导领略下冰川的壮美,二是体会下真正的缺氧”,每个野外人员都想尽力让管理人员了解野外工作的辛苦。我们一路逆着溪水向上,找寻冰川,也想采集到最为纯净的冰川样品。那时的“海拔”是最热的词汇,4800米、4850米、5000米……,大家气喘吁吁,面红耳赤,再看几个身体素质稍差、稍胖的同事,停留在4900米的陡坎上,我们大喊“上来啊,上来了以后格桑花给你唱歌,哈哈哈”。领导们此时都更加平易近人,被我们项目组乐观和过硬的野外实践工作折服。
不冻泉的天阴晴不定,就像小孩子的脸,说下雨就下雨,说下雪就下雪,这为我们雨后测流量和采集降水样品带来极大的方便。记得当时午饭还没结束,外面就下起了雨,我们四人迅速拿起采样专用的塑料布搜集降水,真正做到了饭吃八分饱,健康一整年。
和我们同队的还有两位当地的向导,平时帮我们带路,当地人的身体素质确实好。记得有一次,我们当时走的累的快趴下时,项目负责人说了一句,“不知道山顶的断裂走向变了没有”,我们都傻眼了,心想,让遥感解译一下不行啊,正在这时,小李师傅一个健步开始爬山,那山不算高,但是很陡,过了5、6分钟,他到了山顶,我们让他拍了组照片带了回来,我当时感动的都快哭了,我至今仍然记得他的淳朴可爱模样。
光阴如梭,10年弹指一挥间。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你不是你,我不是我。
如果2008-2009年,你恰巧沿着青藏线旅行,看到三五一群穿着黄皮大衣,带着雷锋帽子的年轻人朝着火车挥手,那十有八九是我们;如果你看到一辆皮卡后轮陷在高山草甸的沼泽里面,我们四处捡石头垫车轮,那十有八九是我们;如果你看到手拿地质锤看到出露的岩石就砸一砸,不砸出新鲜面决不罢休,然后还要拿出另外两大件围绕新鲜面来回折腾的,那十有八九是我们;如果你看到有人在青藏线拿着尺子测量道路的宽度和高度,那十有八九是我们;如果你看到一群年轻人拿着三角堰或者测流尺逢水沟必测,那十有八九是我们;如果你看到一群年轻人拿着红皮本、2H铅笔对着崩塌导致出露的管道又描又记,那十有八九是我们;如果看到一群年轻人誊写卡片、反复修改不下5次,直到水文地质要素、环境地质要素全部在剖面上展现才肯罢休,那十有八九是我们;如果你看到一群年轻人手舞足蹈地坐着皮卡在下山的路上回格尔木洗澡、修整,那十有八九是我们;如果你看到一群年轻人扯着党旗拍照,还摆出“二很胜利”的手势,那十有八九是我们。
镜头拉向2010年,我由于身体原因,不能继续上高原了,就转向了二氧化碳地质储存调查这个新领域。凭着这些年广泛接触的领域,杂七杂八的,正适合干这个跨度大、融合性强的新型专业领域。告别了野外工作,开始开展大量的综合研究工作,主要针对国外已经开展的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方面的图件编制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项目组十人凭借着“二氧化碳地质储存潜力评价与示范工程”项目共同拿到了地质调查一等奖。同时,我的第二个儿子也来到了这个新奇的世界。
穿越结束,回到当下,我退守在办公室的新闻宣传岗位,我要做的是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好单位的新闻宣传工作。
我要用地质工作实践者的视角更深入地挖掘他们的故事,挖掘他们身上含蓄的地质文化。因为我知道,每一个不善于表达的灵魂深处,都积聚着能量,每一个特立独行的灵魂背后,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的地质事业需要他们,我们的科技创新更需要他们,他们没有浮夸,没有浮华,有的只是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这样的人是我们地质工作的脊梁,是地质文化真谛传承的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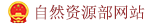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433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202007433号